二零二零七月几则
life沉默的中年
抓一本最轻薄的书塞进包里,坐上前往北京的高铁。与之前数次“抖音之旅”体验不同,今天气氛格外沉默。
右边坐着一位接电话的工程师。他穿着运动服和运动鞋,头发凌乱而稀疏。他先和电话那头确认了“数据集容量”,又聊了许多“神经网络参数”改进的建议。我不由自主地看了一眼自己的运动鞋,挠了挠头。
左边是一名中年男人。他戴着精致的眼镜,穿着优雅的皮鞋。他踩了我一脚,却一直沉默着。我想可能是世界亏欠中年男人太多,让他们惜字如金。我抽出《嵇康之死》,它的封面绿油油得,夹着我喜欢的塑料书签。中年男人随即也捧出一本《红色的起点》,它的封面红彤彤得,夹着烫金的金属书签。
《嵇康之死》很有趣,约莫四个小时我就读完了。把书放回包里,我又对中年男人读的那本“红书”起了兴趣。打开手机搜了搜,在看到作者名时却愣了神:叶永烈 著。叶先生的作品:《十万个为什么》填满了我的童年,《小灵通漫游未来》着实令人啧啧称奇。我今天才知道,他还写过这么多红色传记作品。查了查 wiki,对他转写传记的动机哭笑不得[1]。
戈多
“挤下火车,挤上地铁。”原以为我会经历这样的事。但不知是不是疫情原因,地铁上空位还算多。上一次乘坐北京地铁是十余年前,彼时我对北京地铁印象极差:狭小的空间,吱呀呀的吊扇,还有许多灰尘。现在当然不一样了:干净整洁的车厢,赛博朋克风格的残影广告,处处透露着大城市的光洁靓丽。
我从大望路站走出地面,迎面是一栋方头方脑的建筑,名曰北京 SKP。上网搜寻了一下,得知它是一个“高端百货卖场”,我便来了兴趣:刚来北京,添置一些质量上乘的生活百货总是有必要的。但我真正走进去时,却眯起了眼。我疑惑,究竟是什么收入水平的人,会把大众认知的“奢侈品”称为“百货”呢?这里的衣服、背包排列的十分整齐。整齐得有些刻意。
走到路口,我又看到了另一种整齐。
我先是与其他行人一起,停顿在红灯前。突然如发令枪响一般,人群冲了出去。我仔细揉了揉眼睛,确认信号灯的颜色没变,而我也没理由在瞬间患上色盲症。我在疑惑中环顾四周,刚才熙攘的人群已不复存在。但好在剩下零星的“顽固派”们面面相觑,证明了自己并不是邪恶的那一方。
“三五分钟”很多时候被用来表达时间短暂,但真在红灯前灯罚站这么久,可就让人精神恍惚了。也难怪有那么多被生活赶着向前冲的人,忘记了如何等待。
那是这个城市不成文的规矩。
视线
北京一样有酷爱展示自己的腰线和大腿的姑娘。我骑着单车漂流在街上,总会聚精会神地盯着前方的路,这就导致经常有上述情景闯入我的视线。我不会说我不喜欢,那样显得虚伪。但这样不许我有心理准备的唐突视觉冲击,却总让我想起《维纳斯的诞生》。我只好慌忙移开视线。
迁徙
住了几日,观察到一种迁徙现象:不同品种的野生单车会在不同时段结伴迁徙。上班时,他们从小区门口飞往公交地铁站,下班时,又有序的返回小区门口。
早上若是稍微出门晚了一些,就会被迫成为穿行在钢筋水泥丛林中的猎人,猎取目标正是一辆健康的共享单车。老猎人们都有着敏锐的嗅觉,能飞快的赶往单车聚集区,甚至可以一人跨坐两匹,同另一位姗姗来迟的猎人朋友分享。而新猎人,比如我,则会掉进单车们报复的陷阱里。新猎人常被路边落单的车吸引,加速赶去,如骑兵跨上战马,正待扫码登记战果,却无奈的发现,这辆车不是爆胎,就是缺个踏板,总之是无法冲锋陷阵。
这大概是单车们对日夜连续劳作,还要被 gps 定位的反抗吧。但话说回来,这些反抗的单车,因为检测修理成本高过重新调度的成本,最后好像都被遗弃了。
云与微波炉
我在有空调的楼房里工作,少有机会与阳光亲密接触。于是遇上晴天的早晨,我会在下公交后展开身体,抬头看着云,像微波炉里的食物一样旋转自己。
y2k时代的扫地僧
每当大脑过载需要休息时,我会拿起扫帚,开始晃悠悠的扫地。地上的灰尘和阻碍我思绪的东西仿佛产生了量子纠缠。扫帚每划清一块区域,大脑也会跟着轻松一截。
工作前,长辈们经常向我分享经验:「去了公司要勤快,有时间主动干干杂活,早起去烧壶水、打扫卫生,给大家留个好印象。」虽然我对刻意地勤快没什么好感,不过扫地算是我的爱好,倒也乐意。
现代化的公司没有给我这个机会:这里分饮水机和咖啡机,还有专门的保洁阿姨。我能做的就只剩把自己的工位收拾整齐,午餐吃干净。
save the world
叶永烈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,却成为了中国著名的科幻、科普、传记作家;一些同事也说自己的专业和职业关联不大。但我想,人要活那么久,如果只能从事学生时就固定下来的职业,岂不是太无趣了?别让学习限制自己的可能性啊!
…
目前为止,我不讨厌这个城市。
但我总是早早醒来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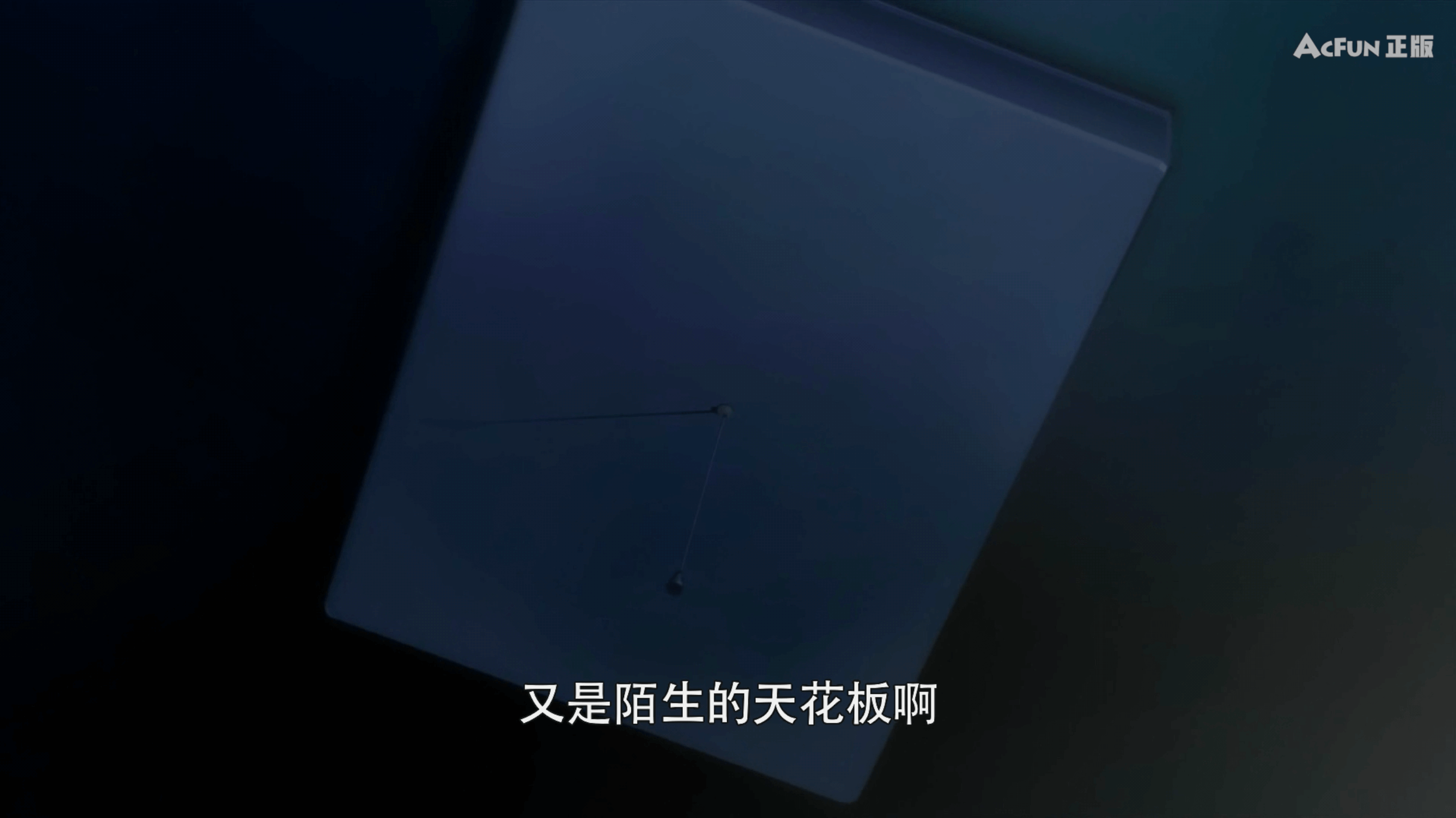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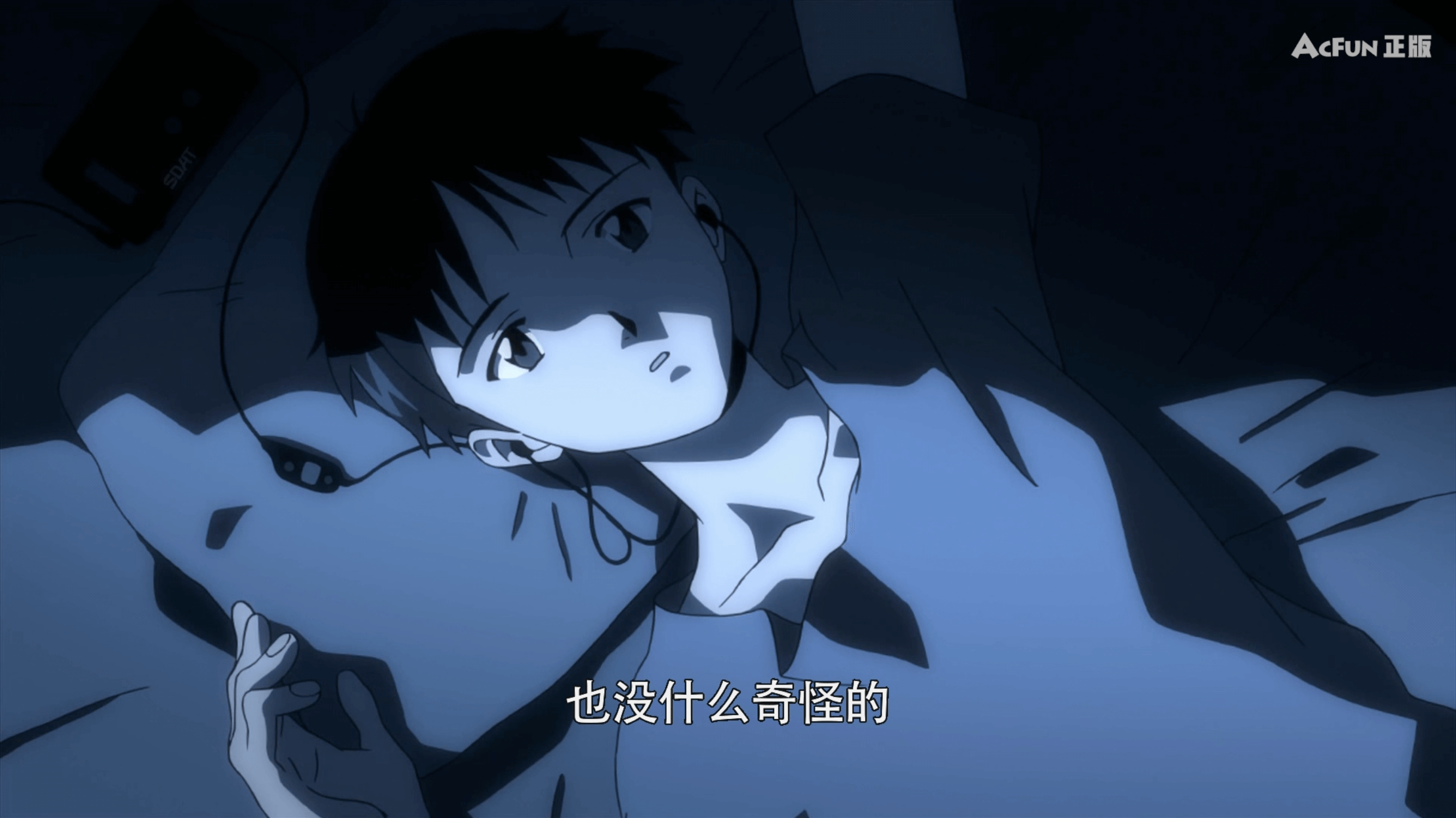

注
[1] wiki: 但1983年开始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严重影响了当时中国的科幻小说事业。保守派声称,有不少科幻小说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,在青少年中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污染。叶本人的作品《黑影》也在1983年11月3日的《中国青年报》上被点名批评。之后迫于种种压力,叶永烈被迫放弃了科幻小说的创作,转而写作传记文学